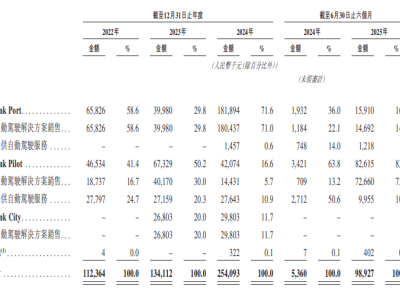在浩瀚無垠的宇宙中,一張照片始終占據著“最震撼太空影像”的榜首。畫面里,深邃的黑色宇宙背景中,一個渺小的白色身影孤獨地漂浮著,沒有繩索的牽絆,沒有安全線的束縛,仿佛一粒被遺忘在虛空中的塵埃,靜靜地懸浮在地球那巨大的藍色弧線之上。完成這一壯舉的,是布魯斯·麥坎德利斯二世,他因此成為了宇宙中第一顆“肉身衛星”。
時間回溯到上世紀70年代末,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(NASA)正滿懷憧憬地規劃著航天飛機時代的宏偉藍圖。他們期望未來的太空任務不僅能進行觀測,還能對衛星進行維修和回收。然而,這一愿景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技術挑戰:如何讓宇航員在太空中自由移動,而非像被繩子拴住的風箏一樣只能圍繞飛船附近活動?
為了攻克這一難題,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裝備應運而生——載人機動裝置MMU。它看起來既笨重又充滿未來感,宛如一把白色的“太空椅”。MMU高約1.2米,重達140公斤,背部配備了24個微型氮氣噴口。宇航員只需通過扶手上的操縱桿,就能向上下左右前后六個方向噴射氮氣,從而在三維空間內實現自由飛行。
然而,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,這項創新被視為“自殺式”的嘗試。太空中的物理法則既神秘又危險,這里沒有空氣阻力和摩擦力的約束。一旦MMU的某個噴口發生故障持續噴射,或者宇航員操作失誤導致旋轉,他們將像失控的陀螺一樣在真空中無休止地翻滾,甚至徑直飄向宇宙深處。沒有安全繩的庇護,意味著一旦燃料耗盡或機械故障導致無法返回,航天飛機很難在短時間內變軌去“捕獲”一個渺小的人體,失控就意味著成為永遠漂泊的太空尸體。
盡管面臨諸多反對聲音,布魯斯·麥坎德利斯二世卻始終是MMU項目最堅定的支持者和推動者。他是一位兼具卓越工程師素養和資深宇航經驗的專家,早在阿波羅計劃時期,他就擔任地面控制中心的“通訊員”,是阿波羅11號登月時阿姆斯特朗與地面通話的直接聯絡人。對于MMU,他有著深入骨髓的了解。從設計圖紙到每一個螺絲釘,從流體力學到控制軟件,他參與了這款設備研發的全過程,對每一個零件的性能和每一個可能的故障都了如指掌。
在長達10年的準備時間里,布魯斯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訓練。他在模擬機上進行了成百上千小時的重復操作,預設了推進器卡死、陀螺儀故障、氧氣耗盡、通訊中斷等所有可能發生的恐怖場景。他訓練自己在極度眩暈中保持冷靜,在黑暗中盲操復位。NASA的同事們曾評價道:“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個人能獨自飛到太空深處,然后再活著飛回來,那這個人一定只能是布魯斯。”
1984年2月3日,美國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,巨大的轟鳴聲劃破長空。布魯斯·麥坎德利斯二世搭乘“挑戰者號”航天飛機沖入云霄,開啟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太空之旅。而他要完成的,卻是前無古人的“無繩行走”。
8分32秒后,“挑戰者號”順利抵達約300公里高度的預定軌道,以每秒7.8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繞地飛行。四天后,2月7日,歷史性的時刻來臨。氣閘艙的門緩緩打開,布魯斯背著巨大的白色MMU,像一個背著殼的蝸牛,緩緩飄入真空。他的面前,是深不見底的黑色宇宙;他的身后,是高速掠過地球表面的航天飛機。
他仔細檢查了所有儀表,深吸一口氣,然后做出了一個讓地面控制中心所有人心跳驟停的動作:他解開了那根維系生命的系繩。隨著手指輕輕撥動控制桿,MMU后背噴出無形的氮氣流,布魯斯開始緩緩遠離“挑戰者號”。他離飛船越來越遠,最終達到了約98米的距離,創下了至今為止人類與載人飛船之間的最大距離紀錄。
在這個距離上,“挑戰者號”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玩具模型,而布魯斯周圍是絕對的寂靜和空曠。他在太空中懸浮了近6個小時,其中有30分鐘是完全脫離飛船的自由飛行。后來在回憶錄中,布魯斯描述了那種震撼靈魂的體驗。他說,當他獨自一人漂浮在寂靜的虛空中,低頭俯瞰那顆藍色的星球時,一種被稱為“總觀效應”的感覺擊中了他。“那里沒有國界,沒有戰爭的硝煙,沒有種族的對立,也沒有顏色的紛爭,只有一顆美麗、脆弱、鮮活的藍色星球,在黑色的天鵝絨背景下緩緩轉動。”那一刻,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,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偉大。正如他在無線電里那句發自肺腑的感嘆:“我從未感到如此獨立。”
在完成了預定的測試動作后,最關鍵的返航時刻到來了。在沒有阻力的太空中,減速和剎車比加速更難。如果速度控制不好,他可能會撞毀在航天飛機上,或者擦肩而過飛向深淵。布魯斯憑借著千萬次訓練形成的肌肉記憶,精準地操控著氮氣噴射的頻率和方向。他調整姿態,緩緩轉身,對準了氣閘艙。隨著最后一段氮氣噴出,他穩穩地停在了機械臂的抓取范圍內,成功與飛船對接。那張由他的隊友從駕駛艙拍攝的照片:一個渺小的宇航員,孤獨地懸浮在巨大的地球之上,迅速登上了《時代周刊》等全球各大媒體的封面,成為了航天時代的精神圖騰。
雖然MMU裝置后來因為安全風險過高而被NASA永久退役,被更安全的機械臂和系繩系統所取代,但這并沒有削弱布魯斯壯舉的光芒。那張照片反而變得更加珍貴和絕版,因為它定格了人類探索史上一個不可復制的瞬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