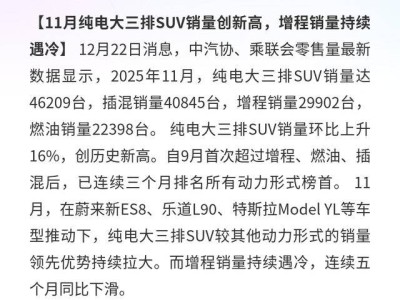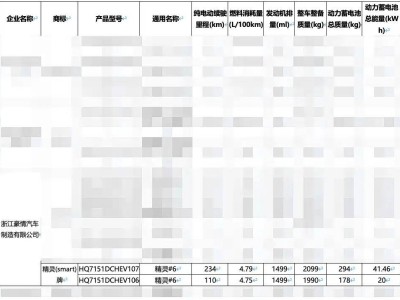杭州,這座曾以“直播電商第一城”聞名的城市,正經歷著一場靜默的行業變遷。從向太、瘋狂小楊哥相繼退租,到辛巴團隊遷回廣州,再到麗晶國際等“網紅大樓”租金大幅下滑、人流量銳減,關于“主播撤離杭州”的討論持續發酵。盡管本地媒體強調網紅凈流入仍呈增長態勢,但從業者普遍感受到的,是投流成本攀升、轉化效率下降、退貨率居高不下帶來的生存壓力。中小主播的生存空間被快速壓縮,行業正從野蠻生長轉向存量競爭。
2018年至2021年,直播帶貨迎來黃金發展期。消費者信任度高、沖動消費普遍,品牌方預算充足,行業乘著流量紅利迅猛擴張。杭州憑借成熟的供應鏈、密集的電商人才和完善的物流體系,成為無數從業者的“淘金地”。據浙江省商務廳數據,這座城市平均每244人中就有一位帶貨主播。陳若藍正是在這一時期來到杭州,她回憶道:“當時市場供不應求,只要敢上播、會吼單,即使技巧生疏,也能立刻看到成交量。”她曾月入近5萬元,甚至見證過有人三個月賺到30多萬元。梁晨的經歷也印證了當時的狂熱——她從北京外貿行業轉行至杭州做直播運營,發現兼職主播時薪遠高于原行業,便果斷裸辭加入。
那幾年,麗晶國際、濱江、奧體周邊成為直播產業核心區,“一棟公寓住三萬人”的傳言雖夸張,卻折射出行業的瘋狂。新人運營底薪2萬、主播底薪3萬仍難招人的現象屢見不鮮。然而,高速擴張背后,隱患逐漸顯現。李佳琦的“不粘鍋”粘鍋事件、辛巴團隊的“糖水燕窩”風波、薇婭和雪梨的稅務問題,接連為行業敲響警鐘。盡管如此,杭州的吸引力仍未減弱。2021年,在青海做主播的程雨彤因“杭州機會更多、薪資更高”選擇南下,并成功將某兒童鞋履品牌賬號做到類目銷量第一。
但壓力也隨之而來。程雨彤發現,隨著時間推移,業績考核標準不斷提高,“起號不算業績”的公司規定讓她即使做出成績也難以獲得薪資提升。她背負著月成交400萬元、實收180萬元的KPI,長期高壓導致身體亮起紅燈,“因腰疼多次就醫”,她懷疑這與長時間站立直播有關。陳若藍的境遇同樣艱難:今年上半年幾乎未盈利,底薪從2萬元降至1.5萬元,降幅達25%。她坦言:“現在貨品特別難賣,競爭激烈,市場飽和,賬號做起來特別困難。”服裝、箱包等類目的退貨率普遍超過30%,投流成本持續上漲,利潤空間被進一步壓縮。
供需失衡加劇了行業困境。中國職業主播規模已達3880萬人,同比增長1.5倍,行業從“缺人”迅速轉向“內卷”。“你不干,有的是人干”成為現實——時薪50至80元、底薪3000元的崗位仍有人競爭。不合理的合約條款進一步擠壓中小主播的生存空間。許多MCN機構要求主播按比例承擔投流、場地、運營甚至人力成本,導致部分小主播一場直播的成交額連基礎成本都難以覆蓋。林驍從杭州轉戰上海后發現,上海“利潤更高,更靠近品牌總部,高客單價品類機會更多”,這一觀點在社交平臺上引發廣泛共鳴。一條“去杭州還是去上海當主播”的帖子下,多數評論建議選擇上海,理由是“品牌資源集中,機會更多”。與此同時,廣州、義烏等地因成本更低、供應鏈完善,也成為新選擇。
面對行業變局,主播們的選擇趨于理性。離開的人逐漸增多:有人徹底轉行,從事外貿運營、高鐵乘務員等更穩定的職業;有人則換城市繼續直播,核心動力是“別的地方錢更多”。留下的人心態也已改變。周瑤離開原公司后選擇兼職直播,她認為:“全職需要更多機遇,兼職壓力更小。”陳若藍則采取“四線并進”策略:正職、兼職、個人賬號和實體小店同步推進,以分散風險。程雨彤雖對行業仍抱有期待,但也清醒認識到:“未來能生存下來的,要么是官方賬號,要么是頭部正能量賬號,小賬號真的很難。”
這場行業變遷映照出直播帶貨從“風口生意”向“專業經營”的轉變。主播的角色不再只是追趕風口的人,而是必須在更成熟的行業結構中重新定位的職業者。逃離、觀望與自救,三條路徑共同指向一個結論:直播帶貨正在褪去神話色彩,回歸商業本質,未來的增長將更依賴于可持續的經營能力。